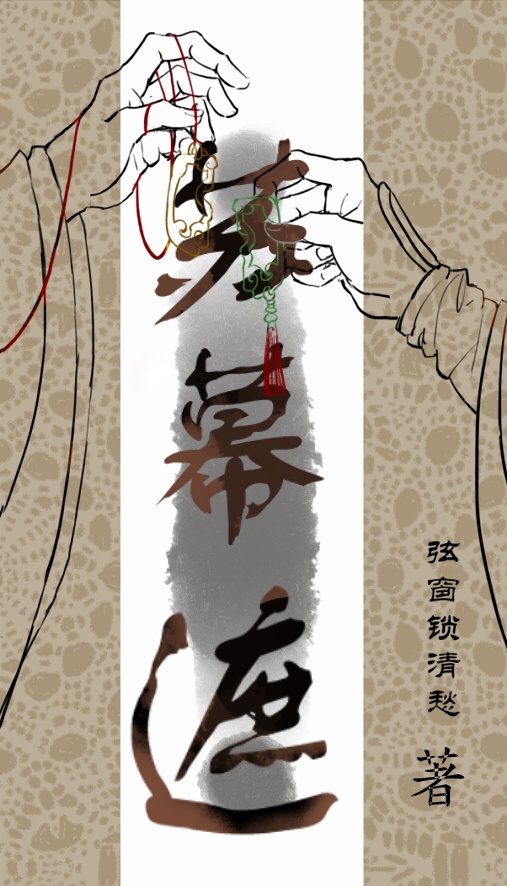“壮气——直冲牛斗——乡心倒挂扬州——”①
河清头疼地听着台上传来的声音,倒不是他不喜欢听戏,就是——这唱得也太不好了,虽然也不是不能入耳,但同他往日听过的相比,就连之前在邱应那里听的才搭起来不久的草台班子也比这个好,也就是扮相好看。
难怪生意这么差。
他撇撇嘴,移开视线,抱臂又往门口退了几步,试图远离声音的来源。
只可惜,羡王就坐在台下,河清这个随侍要当心主子的吩咐和安危,再怎么逃也逃不到哪去。
虽然河清对戏班的水平十分怀疑,且对那台上的戏子实在是敬谢不敏,可大多数人听戏都是图个热闹,看看故事,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些趣味,哪里会像河清这个跟着羡王惯了的人这么讲究?是以,虽说这戏班子实在是不尽如人意,但戏台下的位置还是被坐满了大半、不过,听戏向来不只是听戏,更是为了和旁人交流,就着机会拉近彼此,戏的好坏有时还是其次。
虽然被坐满了大半,但总归还有位置可坐。河清捡了个位置坐下,正好在宁钰忍位置不远处。桌子上摆着些糕饼水果,河清捡了个大橘子,慢慢剥皮。
橘子破开的清甘气息让人心静神宁,河清撕开一片橘皮,果皮和橘瓣间联结的白色须络根根断裂,裸露出的部分果肉饱满。他看了眼斜前方王爷的侧脸,十分惆怅,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自家王爷怎么转了性子,连这样的戏都看得下去。
上次他老人家不是还将京中一个戏园子讽刺得没脸见人了么?那家戏园几天后就搬离京城了。人家唱得可比这好多了。
今日上午,羡王一反往常地没有去绣雁。虽说唱戏的少有几个早起的,大多都得等到下午才能听见响动,可罗檐本职不是唱戏,他的作息和常人差不多,又因为此时人少,羡王大多时候也这个点去找他,虽然河清觉得罗公子似乎不大愿意见自家殿下。但羡王今日早晨出门,带着河清逛了大半天,把渚州白日开门的戏楼都去了个遍。
这是最后一家。
河清掰开手中的果肉,拨下一片清甜多汁的橘瓣放入口中,轻轻一咬,果肉中的汁水在舌尖绽放。他不禁赞许地点点头,虽然戏不好听,可这戏楼里的吃食还真不错。
唉,殿下都在这儿坐了一个多时辰了,还不走吗?河清看着羡王的侧颜,在心中无奈地叹了口气。
哪知,高高在上的老天今日似乎打算对他发发慈悲,河清正这样想着,之前安坐如山的亲王殿下却突然起了身,向这边走来。
河清连忙扔掉橘子,站了起来:“郎君?”
“你不是很无聊么?”宁钰忍摩挲着手中小巧的玉牌,脸上慢慢浮现出笑意,不等河清开口否认,他就低声道,“正好,咱们去找有意思的。”
河清闭了嘴,他用脚趾头猜都知道要去哪。
——
——
未晞已经非常眼熟羡王和羡王手下的人了,甚至偶尔还会搭一两句话,又没少从白露那里得羡王殿下的好处。俗话说,“吃人嘴短,拿人手软”。未晞现在别说拦着这两人了,连当着他们的面提前跑去给罗檐报信都不好意思。宁钰忍带着河清如同回自己家一般,十分顺利就来到罗檐的小院外。要是厉莲生在这儿,八成回觉得羡王殿下在这儿和当初逛御花园没什么两样。
小院院门半开,从门外就可以看见院内的情形。
罗檐站在院子里,正同一个中年男人说话,似乎在讨论什么事情。宁钰忍看了眼,发现那并不是周温汝。绣雁的东家周温汝是罗檐的舅舅这件事,宁钰忍一清二楚,他也见过周温汝。
见过后,他对罗檐戏台下这一身书卷气的来历也不奇怪了,也许是跟着周温汝养出来的也说不定。
宁钰忍勾了勾唇角。院内的谈话似乎已经结束,中年人从门内出来时,被站在门扉前两人吓了一跳,他不认识羡王,只以为这是罗檐的什么朋友,行了个常礼致意,就离开了。
“这是绣雁的总管事。”河清低声道。
右手执着合起的折扇在左手心亲亲敲打,宁钰忍看着中年人远去的背影,抬手,敲了敲门。
青年原打算回屋,听见了敲门声,便止住脚步,却见羡王殿下脸上挂着笑,从门外闲适地漫步进来。戏子霎时变了脸色,微微翘起的嘴角也抿直绷紧了,一副大敌当前的模样,微垂的长眉又显露出几分无奈来,让羡王心觉有趣。
羡王一觉得有趣,就要引得对方多说几句给他逗趣:“罗兄,原是特意在这儿等我的?罗兄如此看重我这个朋友,实在是让人感动。”
这还不算完,他上前几步,道:“罗兄怎么知道我这个时辰来?我害怕罗兄不在呢。这难道就是书上说的心有灵犀么?”冷不防,宁钰忍就去捉罗檐的手,脸上却没显出半分其他情绪,仍旧是笑意盈盈的一张俊脸,“我今儿才是长见识了。”
罗檐要躲,却没躲过,被宁钰忍捉住手,外人看来,一副宾主尽欢,密友情深的模样。青年心底不觉生了怒意。他最开始原是打定主意对宁钰忍不冷不淡,可人家说,泥人也有三分气性。时间久了,两人也算熟了起来,习惯一有,罗檐架子就被拆了三分,哪里还端得起来?瞧见宁钰忍也不自觉带了些性情出来。
你这是把我这里当消遣了?罗檐心想。可伸手不打笑脸人,他还得应付着。
“王爷说笑了,”他试了试挣脱对方的锢桎,却收效甚微,只得遂了对方的意,与羡王殿下“把臂同游”,“殿下里面请。”
一壶茶煮下来,罗檐心里的火气就消了。他早已不是早些年那傲气的性子了,不过是与昔日的友人亲近些,比起真正的磋磨,实在是不值一提。
自己前些日子真是魔怔了,见到旧人旧事就慌了手脚。
何况,宁钰忍又不晓得他是谁,既然不晓得,那又有什么好在意的?罗檐自哂一笑,心平气和地倒了两杯茶。
宁钰忍坐在上次帮白露看字帖的位置,左手支着下颌,冷眼看着罗檐忙碌,面无表情,不知道在想什么,白光从窗格中照进来,在他俊美的脸上流转,显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冷漠和苍凉。
等到对方抬起头,他微笑着接过戏子递来的茶。
“殿下今日怎么这个时辰过来?”罗檐真正心平气和下来,反而没了之前的诸多烦恼,毫无顾忌地开口。
宁钰忍好像也察觉到了了他这种变化,也不再故作姿态,收起了调笑,恢复成马车上那个高高在上的羡亲王殿下:“本王临时起意。”
青年看了他一眼,心中想,他何时有了这变脸的毛病?
羡王在手中转了转木杯,微微歪头,问了罗檐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:“你不喜欢吃甜的?”他盯着罗檐的脸,似乎不允许戏子回避,要将青年的神情尽收眼中,将回答真假勘探清楚。
“是。”罗檐的目光落在宁钰忍腰间,微微一凝。
“为什么?”羡王问。
“只是不喜欢,”罗檐端起茶,不动身色地将停顿了一阵的目光收回,在对方的凝视下,他又加了一句,“太腻了,吃起来头晕。”
羡王支起下颌,没有说信不信,看了这戏子一会儿,突然开口问:“喜欢吗?”声音如朗月清风,让人沉醉。
罗檐没搞明白:“什么?”
他低下头,取下腰间的玉牌,微微前倾靠在小案上的上身,靠近罗檐。小案本就不长,宁钰忍的手抬到两人中间,罗檐能甚至能看清对方手指上金指环的花纹。宁钰忍一松手,一枚小巧玲珑的玉牌垂坠在两人中间,距离彼此的面庞,不过咫尺。青年的瞳孔不觉一缩。
“你喜欢它吗?”羡王问。
玉牌微微摇荡,罗檐感觉对方喷吐的气息拂过了自己的面颊。
“我第一次在通判府遇见过你吧?”宁钰忍微微笑了起来,他放低了声音,像是在倾吐什么秘密,春水退去,湖底致命的尖冰终于显示出了行迹,绮丽的画皮下,剖心的怪物笑了起来,“你看过它很多次,每次我把它戴出来都是。”
罗檐垂下眼睫,敛起了话语中的情绪,吹皱杯中的茶水:“漂亮的东西,谁不喜欢?”
“还有另外一枚,同它是一对,”羡王眨了眨眼,那双漂亮的眸子似乎要将人溺毙,“罗檐,你见过么?”
“因为只见过这一个,才觉得格外漂亮。”戏子抬起眼睛凝视近得呼吸可闻的脸庞,俊眼修眉,似清醒似毫不知情,“更何况,殿下的东西,我怎么可能见过?”
“是吗?”宁钰忍微微一哂,伸手拨开罗檐脸庞前的发丝,抚上他的脸,宛如在对挚爱吐露爱语,他换了种甜蜜的称呼,像是上好的鸠毒,“阿檐,没见过才好。”低哑如同迷梦的声音,在这寂静中,风一般地吹进罗檐的心底,在上面割出血肉模糊的一刀,掀翻了捆住过往的锁,无数的妖魔挣扎着从泥泞中爬出来索命。
罗檐微微扬起下颌,羡王殿下居高临下地抵住了青年的额,仿佛诸天神佛漫出一点多余的施舍来临幸凡人。
交缠的呼吸没有带来暧昧,反而凝滞了空气和阳光。
“阿檐——”
突如其来的女声打破了这一刻的凝滞,然而其他人的乱入让此刻的氛围更加诡异。
段矜衣的目光落在两个姿势暧昧的青年身上。
“哇。”她说。
第二十一章·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