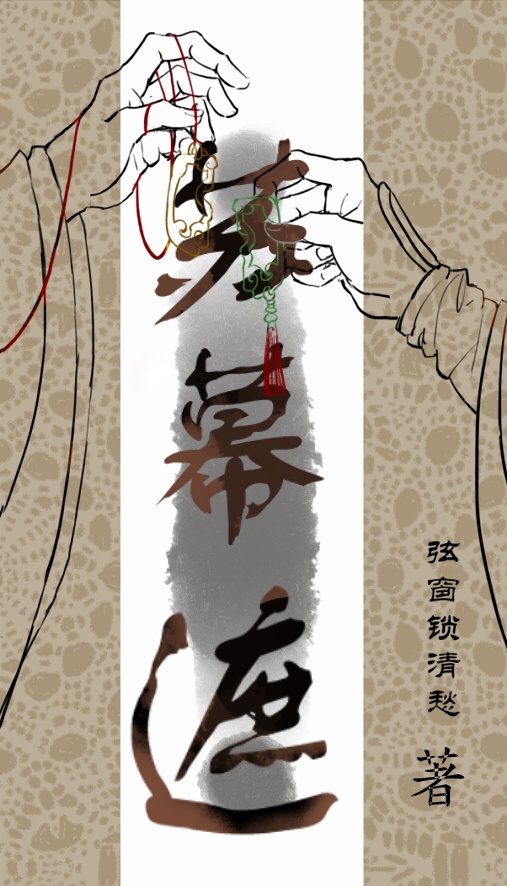李府将戏台设在离岸边不远的一处水榭,岸上连着一处阁子,便将宴席摆在阁子的廊檐下,隔着水远远听戏。周温汝站在台下,他的位置是戏台左侧的一个角落,从他的角度可以看到远处岸上的李闻嵊和主座羡王,却只能从背后看台上诸人。
他瞧见羡王忽然愣怔住了,从不离手的扇子从这位殿下手中摔落,心中一紧,下意识看向戏台上的罗檐。却见罗檐台步极稳,毫不慌乱的模样,可他终究是从后往前看,看不见台上人的脸色,周温汝也因此放不下心来。幸而戏班里年岁小或经历不足的年轻人没有跟过来,否则,若是白露在这里,见周温汝如此不安,这小丫头恐怕回去后又要忧心忡忡得不肯睡觉了。
直等到下台后,周温汝和其他人迎了上去,罗檐面无异色地下台来,只笑了笑,说:“我没事。”便一言不发地去休息了,此后整个夜晚也没说过半句话。
戏毕,周温汝怕夜长梦多,便带着戏班匆匆告辞。他回头看了罗檐一眼,只见青年沉默地待在队伍里出神。
————
李闻嵊送羡王出去。末了,准备上马车的亲王忽然回头对李闻嵊道:“李通判改日去本王那坐坐吧。”
李通判一愣,向来冷峻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,躬身道:“多谢殿下,下官必定备上好礼回拜。”
宁钰忍颔首,钻进马车。待到马车消失在巷口,管家来报已将戏班送走,李闻嵊不甚在意地点点头,转身进门。管家迟疑了一下,跟着往院内走去,看着李闻嵊的背影,忍不住提醒道:“老爷,羡王爷好像是因为今晚那出戏,所以尤其高兴……”
踏上游廊,李闻嵊回头看了管家一眼,他长相端正俊朗,然而成日里神情严肃,显得老成,让人不禁在心里把他那年岁的计算,再拔高了些。夜色正浓,他穿了一身沈衣,只是那双眸子一瞬不瞬地盯着人瞧,让老管家觉得他家老爷的眸子分明比这夜还乌沉。过了一会儿,李闻嵊才转身走远,老管家听到自家老爷的声音从晚风飘入耳中:“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事。”
那词句被风吹得支离破碎,老人站在晚风中,只觉得凉气沁心。
此时整座城池都歇下了,夜深人静,打更人的竹梆子声远远传来,干枯的声音在夜里显得有些苍凉:“天干物燥,小心火烛——”一声一声,在游人散去后空旷的街道上回响,在夜空底下不屈不挠地提醒。
老管家缓缓走入通判府内,听着那打更声渐渐远去,这才关上门。风带着打更声向渚州城的其他角落漾去,漫灌进周温汝的耳朵。
周温汝本想回去后找罗檐问问,奈何夜深,他到时罗檐已经熄灯就寝,只得打道回府。然而,在他走后,雕花木窗从内打开,罗檐在窗边看着院子里的景致,今夜月光如霜,将院子内的一草一木照得一清二楚。月光如水,其中影影绰绰,草荇交横。罗檐洁白的脸上明明暗暗,莫名透出苍白诡谲,烟也似的,好像一阵风就能吹散。夜半转了风向,乌云蔽月,淅淅沥沥下起了下雨,水汽钻进窗内。秋夜寒气深重,加上雨水,罗檐只觉得身上一阵阵发冷。他转过头,点燃了蜡烛,任那烛泪流得诗人断了肠,他静静的在案边坐了一夜。
————
第二天清晨。
齐宣一大早就到处串门,在廊子上头同人家笑骂打闹,到了罗檐这儿,却不见罗檐人影,只有白露一人坐在桌边用早膳。
饭桌上放着一碟白面包子,白露就坐在桌子边边,拿着有她小半个脸大的包子啃。她身量又比一般小孩子小,凳子极高,稍稍坐进去些,脚尖就得踮着。
“小白露。”齐宣跨过门槛,扯了张凳子在饭桌边坐下,“你爹呢?他和哪个小娘子幽会去了?”
白露手上的包子啃到一半,停下来,她早已习惯齐宣这没门把的嘴,却还是认真反驳:“他刚刚去拿粥了。”她顿了顿,小脸很不赞同地道,“大白天的幽什么会?齐叔叔也不好好看戏本,这样不好。”
齐宣被她逗得哈哈大笑,拿了个包子就往嘴里塞。那包子刚买回来没多久,正温热着,表面白胖光滑,个大皮薄,一口咬下去迸出汁水来,满嘴都是扎扎实实的馅料,内馅的香气一下子飘出来,浸足了肉汁的笋干同肉馅、面皮混在一起,齐宣眯了眯眼:“嗯——笋干肉馅的,王大娘家的包子真好吃。”
罗檐正巧端着两碗白粥从外面走来,瞧见他,笑道:“你这大清早的,怎么又来蹭吃蹭喝。”避开齐宣伸过来抢粥的手,放了一碗在白露面前,白露就着罗檐的手喝了一小口白粥,把包子咽了下去。
齐宣没抢到粥,也不气馁,笑嘻嘻地叼着半个包子倒了碗茶,就着热茶水吃:“我这不是好心来看你么?不识好歹。”
青年早就习惯齐宣的性格,嗤笑了一声,拿起一个包子,估摸着白露的饭量,把包子掰成两半,把馅多的放到盘子里,他不动声色地打量了一眼手上的包子,然后开始先吃面皮,慢慢吞吞,状似无事,却微微垂了眼角。
等到白露把那半个包子吃完,开始喝剩下的粥,罗檐还在啃面皮。
齐宣早就解决了包子,倒了第二杯茶,白露擦了嘴,把收拾好的碗筷端走了,罗檐还在和那半个包子难舍难分,如同戏本里的佳人才子,山盟海誓,缠绵至死。齐宣一言难尽地开口:“嘶——你这个人……人家吃包子都要个大皮厚,嫌皮薄馅多的不实惠,要饱人。你倒好,吃包子和吃点心似的,皮厚就不吃,吃个面皮能药死你似的,你知道外头米面多少钱一斤吗?”
罗檐终于把面皮吃毒药似的吃完了,三口两口解决了剩下的馅。他实在讨厌吃面食,吃个包子都能吃出边关将士从容赴死的感觉,只是比起对门王大娘家的包子,其他包子实在难吃,罗檐这才偶尔去对门买几个回来。青年摇摇头,拿起下一个包子,舀了一勺粥,喝下去,道:“这粥也太寡淡了。”
齐宣看着他那勺子在碗里搅和,这粥下了许多米,煮得洁白粘稠,飘着阵阵米香:“你说你,看着好讲话,一接触就发现,满身毛病。吃个早膳吃得跟老李拉二胡似的,要死不断气,难怪段姑娘成日往你这送些吃食,按你这么吃下去,过几天就该形销骨立了。”他把最后一口茶咽了下去,发表结论,“挑挑拣拣的,你上辈子真是少爷命。”
“……”
罗檐斯里慢条地喝粥,在满屋的安静里突然开口:“我没事。”又笑,“你只会安慰姑娘,同人家谈情说爱,满嘴的花言巧语,碰到正经事就没辙了,还不如金熠。”
“行了,齐宣,找芸绣楼的姐姐们玩去吧。”
齐宣冷笑:“谁说我不会安慰男人?林郎君还是我安慰的呢!”
林郎君就是那位送“吃喝玩乐”扇的人才,渚州本地的世家子,本对齐宣有意,奈何齐宣对他无情,这两人私下不知说了什么,摇身一变,成了好兄弟。这位栋梁前几日追求知府家的千金不成,好不挫败,同齐宣等狐朋狗/友哭诉后,去花楼转了一圈,又喜笑颜开,看上了一位清倌,如今正奇珍异宝地供着,每日去也只是瞧瞧,可谓“发乎情,止乎礼”。
罗檐讨饶:“是我言错。”
本也不是真要分辨个明白,齐宣听了这话,又笑道:“这终究是你的事,我本不想多嘴,是班主打发我先过来看看你,这才来的,你别怪我就好。”
听了这话,罗檐才明白过来,难怪今日齐宣一反常态。
齐宣临了顺了个包子:“给金熠带的。”
然而,罗檐看着齐宣熟练地咬了一口包子后,实在怀疑这话的真实性。
最后,这包子到底进了谁的肚子,罗檐也是不得而知了。
————
兴许是因为昨夜下了雨,老天爷为了“雨露均沾”,雨下了不久就住了,太阳出来,鸟雀呼晴,阳光温和,是个好天气。
趁着戏班里大多数人都还没起来,罗檐写了一帖字,写完后,又拿出前几天写的,码好,一并丢进炭盆烧了,洗好笔墨,把砚台放在案上的某个积灰的角落,收拾完毕,这才开了窗。
白露在外边玩,还没回来,青年搬了把躺椅在外边,趁着光阴大好,躺在檐下翻一本不知年份的游记。
这本书也不知放了多久,翻开蓝色的封皮,里面的纸页全都发黄了,又薄又脆,这书都快赶上九旬老翁了,每翻一页都要伤筋动骨,让人觉得它命不久矣,却偏偏怎么折腾都没散架。
作者文笔平平无奇,写事能一句概括绝不多写半句,这样的人合该去给官府写办案公文,写游记真是徒增读者折磨,再加上书上时有时无的油墨味,罗檐看得昏昏欲睡。
“阿檐。”
这一声叫唤得罗檐从周公的棋局上回了绣雁的小院子里,他放下书,定睛一看,笑:“舅舅。”他坐了起来,“你再不来我就睡着了。进来吧。”
周温汝温声道:“不了,我就是来看看你。”他果然只是站着,没有进去,“看什么呢?”
青年把游记递给他:“不知道是哪位高人的书,能把游记写出一股子公文味儿,骈文都比这有趣。”
周班主拿起这书,顺着他看到的地方翻了几页,皱了皱眉,又翻到前面看作者,上书“抱石居士”,他就笑起来:“这个人我认识,后来当了某县县令,如今已然出家了。”
罗檐只觉得匪夷所思:“考官缘何录的他?”那本游记里有几首作者的诗,比平平无奇还无奇,罗公子不敢小看他人,思忖着开口,“难不成他策论十分厉害?”
“非也。”周温汝好笑地摇摇头,“大抵是考官觉得他的文章……古朴?”
罗檐:“……”科举何时如此容易?
万幸周温汝不是为这个话题而来,他说:“齐宣和我说你没什么事。”
“昨夜刚看到他确实恍惚了一阵,后来便好了,毕竟都过了这么多年。”罗檐温和地道,“是我之过,让舅舅担心了。”
这话说得沉静妥帖,也十分坦诚,让人一听便觉得说的人确实心无芥蒂,再加上前几句罗檐说话的态度,本该无事了,周温汝悬着的心却仍然放不下来,齐宣表面上吊儿郎当,其实人情练达,通常不会出错,可周温汝更熟悉罗檐。
“你……”
“齐宣说的我知道,也记在心里。”
周温汝便只得道:“有时出了事,只觉得并无触动,其实心里十分惦念,过了些时日,碰见了某件事,恶果方才显出,你不要不在意。”
他还有别的事,不能久留,只得再三叮嘱:“这几天你也别做其他事了,好好休息,若不行,我把段姑娘叫过来。”
罗檐晓得他是关心自己,都一一应下了。
————
将人送出去,青年坐了一会儿,转眼就到了中午,白露还没回来,也不知道是在谁的院子里吃午饭。早上勉强吃了一个包子和一碗粥,现在五脏庙内空荡荡的,他却半分食欲没有。四下鸟啼虫鸣,人声隔着墙传过来,罗檐却觉得安静得有些寂寞,他像是幼年进宫时看到的那只黄莺,被关在笼子里。
于是他推开门走了出去。
渚州城一如既往的热闹,在拥挤的人潮里,罗檐不知目的,随波逐流。他看着空中的飞檐翘角和曈曈人影,这才发觉,这天地都是牢笼,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,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。
“罗公子。”一道清亮的女声叫住了他。
他抬起头,面前的是一位二八年华的少女,面容秀美,一举一动,状似活泼,却透着规矩的影子,他听见她说——“我家郎君有请。”
罗檐顺势看去,却见路边停着一辆马车。一位有些眼熟的少年站在马车旁,见他望去便低头行礼,罗檐只觉得脑中一片空白,看向那马车的眼神,如同那只黄莺看见了钥匙或者另一个牢笼。
“你是?”
“奴家辞镜。”恍惚间,他听到那少女如是说。